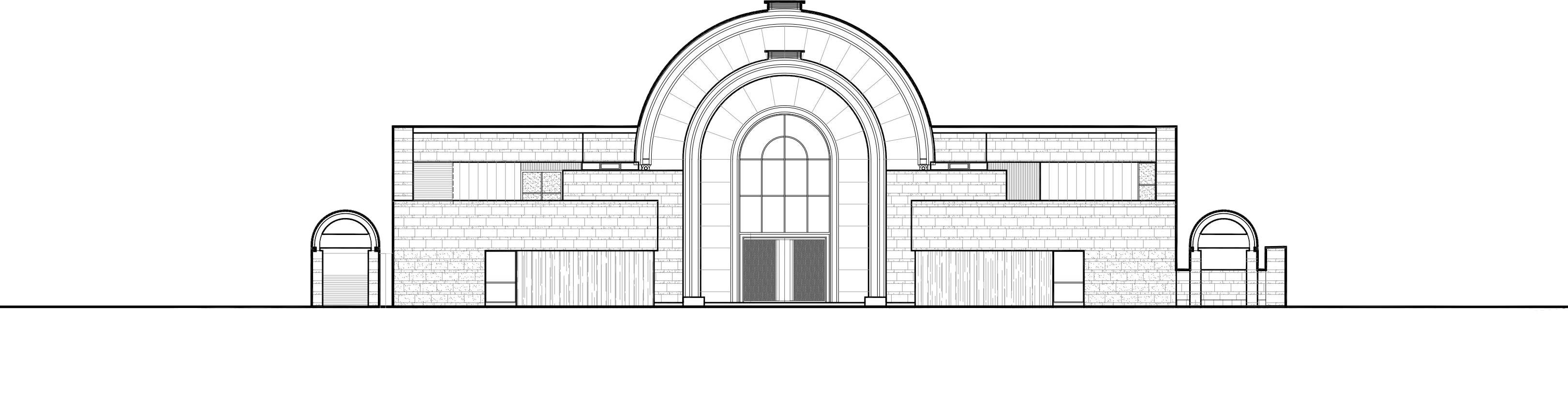我的母親——吳洪起
邱伯蘭
吳洪起是我的母親,生于一八九四年棗莊市南園村一個貧苦菜農家庭。
一九一三年,我母親十九歲出嫁。
我父東邱煥文,也是個沒地沒產的窮漢。祖籍膠東。祖父曾參加過捻軍反清起義。后流落原嶧縣陳家湖安家。
一九〇七年,父親十六歲隨祖父逃荒到蘇北,為生活所迫,入江蘇陸軍第二十三協(xié)當新軍。參加了“辛亥革命”,后回到嶧縣齊村定居。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父親又要扛槍,到賈汪當了警兵。一九一九年他受“五·四”愛國運動影響,登臺演講,反對“二十一條”,排斥日貨,被礦警隊長責打四十軍棍,開除回家。
一九二一年,父來逃到關外,投入張作霖部。六年間,從大兵升至少校團長,率隊駐蘇魯邊。在奉軍期間,響應北伐軍革命,和孫伯英叔權毅然率隊起義,將部隊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蘇魯游擊隊,這支部隊后被蔣介石繳了械。
一九三一年春,父親在徐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四十歲,母親三十七歲。
這年春天,楊樹剛鼓芽,父親從徐州領來兩位“客人”。
我母親奇怪的是這兩個面帶雅氣的比我父親小十幾歲的年青人竟受到他那樣的尊敬。
年青人都儀表端正,衣帽整潔,熱情大方。特別是那個較年輕的,戴金絲眼鏡說滿口南方話的,開口就打趣:
“嫂子!我們是來要飯的”!
“正好,我家剛買了二十畝地,就缺長工,看你敢不敢吃這碗飯。”
“長工!嫂子說對了,我倆就是來當長工的,二十畝太少了,再多的地我們也能種好。”
“客人”抱起我,問我會數(shù)多少數(shù)。還搶著拉風箱,說他沒拉過。
母親同他拉呱了:
“先生家是······”
“湖北陽新縣。在江南,是蠻子,俗話說:“蠻不講理,嫂子以后不能見怪。”
“江南是好地方,我到過蘇州,那是魚米之鄉(xiāng)。”
“江南是魚米之鄉(xiāng),但窮人是吃不上的,跟你們這里一樣,靠地瓜、菜幫過日子,地瓜在我們那里叫紅薯,莊戶人過年時能吃上一碗年飯就不錯了。”
“先生家也種地?”
“我能有那個家就好了。”他嘆了口氣:“我家是富戶,誰知道有多少地,三里五里的都往我家送租,不怕嫂子見笑,小時上學,家里都讓轎夫拾著。”
“你家那么好,怎么舍得讓你出來?”
好個啥,我六年沒回家了。都是人,有的坐轎、有的抬轎,這平等嗎?!”
“說的也是。棗莊中興公司請的德國老毛子不吃糧食,雇八個奶媽子喂他,不平等的事太多了。”
兩個叔叔在我家住下了。后來才知道歲數(shù)大的是中共棗莊特委書記田位東,戴眼鏡的是副書記鄭乃序。
幼小無知的我,除了盼過年,就盼家里有客人。因這時家里就要添一兩樣菜,雖然不能上桌,也能揀些碗底。
一連幾天,父親的好友孫伯英叔叔(嶧西工委書記)也領著王子剛叔叔(在我家宣誓入黨的)來到我家,他倆也同父親一樣,非常尊重這兩個年青人。每當他們聚集一塊時,母親就領著我到院子外,她納鞋底,我看“小雞”,就是看見陌生人走過來就大聲“喚雞”。
黨的工作不可能讓一個幾歲的孩子知道這么多。
父親告訴母親,鄭乃序是假名,他叫陳明道,家是財主,從小是奶媽、丫環(huán)伺候,后到省城讀書,上了武漢大學。參加了共產黨,他家每月給他十塊大洋,他留兩塊搭伙,剩下八塊全拿出來交給黨作為活動經費。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殺共產黨那會兒,要不是他未婚妻報信翻墻頭逃走,險些送了這條命。
“他未婚妻呢?〞母親急切地問。
“被國民黨抓去殺了。”
“他到這兒來······”
“來做工的,過幾天就下井拉大筐。”
“他是大學生,家又是財主,為什么要找罪受?”
“他為的是廣大受苦人求解放。他下井拉大筐就能結識工人,成為工人的朋友,把工人組織起來,就能跟資本家斗,把白日旗換成紅旗,將來就能把落介石打倒。”
“共產黨都是這樣為窮人嗎?”
“不為窮人為自己,就不是共產黨。”
“你怎么不參加?”
“我在徐州就參加了!”
“你是我也是!”
父親笑了。母親默認她自己是共產黨。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也相信自己家里這些為黨的事業(yè)進行活動的人們。
楊樹放花,滿眼青翠。小雞撒歡的爭飼嬉戲,大地沐浴在春暉的陽光里。母來領著我,拿著鞋底到院子大門口“看雞。”
“嫂子:你進屋來!”
位東叔叔親切地招呼著,我可高興了。鄭叔權口袋上褂著個小黑管管,能寫出字來,我老是想玩玩、摸摸,可娘總是要領我去看“小雞”。
“你消坐!”鄭叔叔將鋼筆遞給我,特意將凳面擦擦。
娘笑開了:“啥事勞你的大駕,這么客氣!”
“聽話!挨著我。”
伯英叔是老熟人,鬧慣了。
田叔叔端起一碗茶,送到娘手里:
“嫂子,這些天來,我們在這里又吃又住,看得出來,你是不煩的。你也知道,我們這幾個人要干什么,這樣大的危險,你心甘情愿和我們一樣,我得謝謝你。”
娘察覺父親的幾個“兄弟”有話要對他說,就隨手從屋角拉出了一個小馬凳。
“嫂子,”位東叔叔又把話接過去了。
“你知道了,我們這幾個都是共產黨。共產黨只能為老百姓辦事,不能顧家,今后……”
母親誤解了,說:“你們放心,我向來不管他的事,不怕你們笑話,我十九歲跟他,又一個十九過來了,他在家過了幾天?就只因為窮,到關外,下江南,一輩子當兵就跟槍親,喜歡鬧革命。如今這樣為窮人辦事,我沒有說的。、”
叔叔們都樂了。鄭叔告訴她,共產黨棗莊特委已經成立,田位東是書記,黨委機關就設在我家,黨的任務就是要把棗莊建成紅色蘇區(qū),把抱犢崮山區(qū)建成紅色根據地。
“真有那一天,死也甘心!”
田叔接過話說:“斗爭是不怕死的。我一個人到街上,說自己是共產黨,那早就被抓去殺了。依靠你們幾個,我就不怕有人抓我。我們都去找窮人,把棗莊的老百姓都聯(lián)絡起來,這就不是他抓我,到時候我要抓他。幾千年的皇帝不是打倒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也一樣能打倒。我們現(xiàn)在去聯(lián)絡人不能先說自己是共產黨,說互濟會,是大家伙幫助解決難 事的。這個互濟會首先要掩護黨員進出棗莊,今后經常會有黨員來的,全國都有黨。其次是要籌集款子,我們黨現(xiàn)在沒有錢,黨員來往的路費、吃住都靠互濟會設法。再一個就是要準備萬一黨員叫國民黨抓去,互濟會要花錢活動救人。國民黨的警察、局長、縣長,沒一個不愛財?shù)模M早花錢保出來。”
“互濟會由我當不露面的主任,除了乃序,你們幾位、嫂子你也是。對了,”他轉向我父親:“嫂子叫什么名哪?”
“哪有名!她爹娘沒給她取名。”
“那我們黨來給她取個名好了!”乃序叔接過話,“棗莊有了黨,棗莊要建成蘇區(qū),棗莊要飄揚紅旗,紅旗是我們的希望,嫂子就叫“洪起”吧!”
從此,母親有了名字——吳洪起!
不久,田叔,鄭叔由父親介紹到棗莊中興公司齊家柜下井干了工。孫伯英叔叔和王子剛叔叔到嶧西一帶搞農村工作,黨在魯南的活動開展起來了。這時中共山東省委軍事委員會的程寄平,和濟南來搞學生運動的朱同云,還有姓趙的、姓魏的叔叔都常來我家。
我父親有一張遺稿中記有:“也有上海中央來檢查工作的。有一個駝背四川的同志,說姓張,來棗莊檢查工作。據講中央在上海,周恩來同志領導的。”
這些來的叔叔都在我家找田叔、鄭叔接頭,母親對每個黨派來工作的同志,都象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安排吃住,洗補衣服,她對這些叔叔說:“我家就是你們的家!”
田叔、鄭叔往往從井下帶著滿身勞累和遍體炭污回到家來,尤其是鄭叔,近視眼,下井他不戴眼鏡,到處碰的青一塊,紫一塊,母親見他倆回來又高興,又心疼。
礦區(qū)的工人在田位東、鄭乃序兩位叔叔親自啟發(fā)和組織下,提高了覺悟,加強了斗志,堅信自己能夠團結起來,敢于斗爭就能勝利。
我父親另一紙遺稿中,有這樣幾句記錄:“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春天,棗莊特委統(tǒng)計發(fā)展了黨員十三人,有積極群眾二十多人,建立了老棗莊、金家莊、大洼、田家莊、雷家村、石碑、車站、佟家樓、尤家村、窯神廟、陳家莊,后龍頭、南馬道十三處的通訊聯(lián)絡站”。
娘常領著我到棗莊去“趕集”,行前總是要在發(fā)髻或裹腳布里藏上一張字條,有時回來也帶回小紙條,父親用水一浸,字就出來了。
棗莊不大、中興公司卻不小,它的董事長是兩個赫赫有名的大總統(tǒng)黎元洪和徐世昌,經理是黎總統(tǒng)的兒子黎紹基。
這些大總統(tǒng),大軍閥為何對咱這魯南小鎮(zhèn)——棗莊有如此情感?其原因就是這里有煤,他們開公司,出煤炭,發(fā)大財。眷養(yǎng)了一支近千人的礦警隊護礦,特委的目的是想奪取這支武裝隊伍的武器、拉起工人隊伍,到抱犢崮山區(qū)建立紅色根據地。
母親對進山充滿信心。為了黨進山活動有經費、生活有著落,她將我家的二十畝地賣了二百大洋。她為我收拾了一個小包袱,叮囑我要緊跟大人跑,千萬不能丟了。
娘見我眼淚汪汪,舍不得走,摟住我說:“閨女,咱家隔壁崔家的地主打罵丫環(huán)、逼死長工你都見了、窮人多苦,窮人的苦是地主造成的,為了不受窮,農民佃戶就要和地主斗爭,下窯的工人就應和中興公司的資本家斗爭。鄭叔家里是有錢人家,不在家享福幾千里來咱棗莊下煤窯、拉大筐,不就是要幫窮人翻身,咱進山過人人都一樣的日子不好嗎?”
我似懂非懂,不再難過,詢問起山里有糧嗎?有核桃、梨、柿子、山楂嗎?野花多嗎?
田位東叔叔、鄭乃序叔叔因叛徒佟振江、孟廣銀的出賣,先后被國民黨逮捕了,押到嶧縣城監(jiān)獄。母親非常著急,收拾了兩雙新布鞋、幾件衣服和十塊銀元,要我叔伯哥哥邱伯溪到峰縣監(jiān)獄看望,伯溪哥說:“五嬸您好糊涂,縣府這次辦的是共產黨大案,田、鄭都咬定同任何人沒有關系,人家正找不著咱,咱這一送錢不就找著了。”母親急得直掉淚。
沒過多久,二位叔叔在濟南千佛山下英勇就義的消息傳到我家。母親再也控制不住,放聲大哭。
田、鄭遇難,棗莊特委同上級黨的關系完全斷了。我父母都牢記鄭乃序叔叔臨別前說的:“黨會回來的,會回來的!”
父母將手頭原準備進山的一筆錢拿出來,到棗莊街里開藥鋪,以造成能接近黨的機會(我家原住齊村,離棗莊六里)。
一九三二年秋,南馬道一座兩層的磚質樓房掛上了“同順興中藥店”的招牌、時隔不久,老街也有一家“同春堂藥店”開張。藥店在雞市口的一間草棚,貨只有幾把草藥,幾只缸,但名氣出來了,管事的龐先生妙手回春,藥到病除。
母親裝著趕集,到雞市口偵察了兩次,回來對父親說:“生意倒不錯,進出都是窮人,像滿高興似的。我見龐先生送看病的出來,挺和氣。那模樣比你小幾歲,也留著短胡,你自己去啦啦吧,反正不會是壞人。”
父親隨后去了幾趟,把龐先生領到我家、“龐沛霖”是郭子化的化名。郭叔叔對我家經營的“同順興藥店”非常滿意。這幢兩層磚質樓房,它在五十年前的棗莊是小有氣派,非常便于同志們往來住宿。是理想的黨的地下機關。
一九三三年“五一”罷工勝利后,礦區(qū)黨委在“同順興藥店”的樓上正式成立。黨委決定“同順興”改名為“中西藥品運銷合作社”。
我家有“中藥”有“西藥”,什么人都可以來往。有“運”有“銷”,什么人都可以居住。
“合作社”掛招牌那天,鞭炮響著。
人們議論著:邱家發(fā)了,生意真好!
是“發(fā)”了。你看一天到晚看“病”的,抓“藥”的,送“貨”的川流不息,白天開 “洋匣子” 聽戲文,晚上點“自亮燈”。
叢林(他讓我喊他大哥)首先從沛縣調來棗莊,以后郭致遠叔叔也來了,他們比我哥哥大幾歲,都是黨的主要工作人員。“合作社”經常住的滿滿的。
粉碎“四人幫”后,郭致遠叔叔到泰安干部療養(yǎng)院看我母親,母來做了飯,致遠叔端起碗說:“老嫂子,四十多年前,您就給我做飯,今天我要多吃一碗!”
是的,三十年代我母親就是邊區(qū)黨委地下機關的炊事員和通訊員,她天天要烙餅,頓頓要燒湯,夜夜要洗衣服,難得有閑著的時候,活,是那樣的勞累,而她干得卻是那樣高興。
“七、七”事變,華北淪陷,祖國的半壁河山已在日本強盜的鐵蹄之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侯,何一萍叔叔來到我家,這時邊區(qū)特委和郭子化叔叔已遷徐州,棗莊設立了魯南中心縣委,一萍叔是特委委員兼中心縣委書記,機關仍在我家的“中西藥品運銷合作社。”
日寇逼近,蔣介石的國民黨被迫宣布:“抗戰(zhàn)”,對付共產黨人的屠刀稍有收斂。何一萍叔叔具體領導棗莊及魯南地區(qū)的抗日救亡運動。
我當時上小學三年級,學校停了課,小學生也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我參加兒童團,學習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和《長城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棗莊抗敵后援會主持召開了四萬人的誓師大會,韓文一叔叔上臺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揭露了國民黨不抵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母親拉著我就在人群中,她沒有激動地呼口號,也沒有沖上臺去講幾句話,她站在那里,成了淚人。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們隨抗日義勇隊東征,到達四縣邊聯(lián)的高橋、大爐根據地。
我們進了山,父親到義勇隊工作去了。母親帶著哥哥伯達和我來到徐莊。開了一家藥店作為黨的聯(lián)絡點,母親在藥鋪生活多年,對中草藥也稍有認識。哥哥伯達開始參加了黨的工作。日本人進不了山,飛機到處狂轟濫炸,一天對徐莊轟炸好幾次,有一次炸彈投到我們藥鋪,三口人都被土墻埋住了,是人家扒開磚土救出來的。
棗莊的家被日寇占領了,徐莊的家被日本飛機炸塌了。
日本強盜的暴行,“中央軍”的潰逃和搶劫更加激起了人民群眾抗日救亡的怒火,不久,哥哥也離開我們,直接到抗戰(zhàn)的第一線。進山后,所制的中藥大部在多次遷移中損失,少部份由我母親攜帶以賣藥作職業(yè)掩護之用。原藥品合作社的股金屬一般社員的都在撤退前還給了社員,剩余的部份大部為張毓昆先生的投資,其余一部分屬我家的資金。當父親和母親商量將西藥工具和器械交義勇隊時母親也極表同意。父親還說張家的資金目前不能償還了,只好等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了用抗戰(zhàn)的勝利來還良心賬吧!母親領著我,背起藥箱,裹緊小腳,踏遍了抱犢崮的山山水水,一邊搜集敵偽活動情報,以便選醫(yī)送藥到山村,她是菜農出身,農活在行,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一邊干一邊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發(fā)動組織婦救會。抗戰(zhàn)時期,抱犢崮的群眾,大多數(shù)都知道“邱大娘”。
一天,父親回到我和母親臨時居住的外峪子村,問我是參加抗戰(zhàn)還是跟在母親身邊?這個不算突然的問題,突然提出來,我為難起來,真舍不得離開母親。
早晨起來,娘替我梳頭。心情有些激動,叮嚀我要記住田叔叔、鄭叔叔。
一滴淚水就滴在我的脖子上,我也哭了。
起程路上,娘叮囑我不要想家。
“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子,我們才能在一起”。
離外峪子已有幾里地了,娘停下來,那顫抖的手再次為我理理頭發(fā):“跟著你爹,一直朝前走,別回頭。”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三周歲的我,按照母親的囑咐,跟著父親,奔向抗日救亡的戰(zhàn)斗行列,成了魯南軍區(qū)宣傳隊的一名戰(zhàn)士。
“一直朝前走,別回頭”。這是母親送我走進革命大家庭的贈言,也成了我終身的座右銘。
有的材料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我母親于一九四一年,四、二五事變,國民黨進攻,鬼子掃蕩,積蓄五塊錢,拿出買米做飯,支持黨員偵察敵人,打了勝仗。
國民黨卻乘春荒之際侵入我根據地,邊區(qū)縣被壓縮到一槍能打透的“一線牽”的狹長地帶。母親同劉清如,葛成俊、荊守勝等同志一起,堅持在這里。
魯南事變時,我隨軍區(qū)主力較移到鄒縣地區(qū)十八趟。離開根據地后,給養(yǎng)更困難了,我們宣傳隊只有摘野果,喝溝水來解決饑渴。很快,嚴重的疾病流傳開來,不少“小鬼”都身躺山坡,再也起不來了。我也病得很重,卻不知是怎樣活過來的。
在這段時間里,母親也聽不到父親、哥哥的消息,時刻惦念著。還聽人傳說,我們軍區(qū)宣傳隊的孩子們,在過敵人封鎖時,均被敵人機槍打死了。她心如刀絞,天天流淚,盼望能聽到準確消息。
半年后,我隨主力部隊又回到抱犢崮根據地。娘聽說宣傳隊回來了,早就等在我們行軍途中的路口,當她從“小鬼”的隊伍里認出我來時,一把抱住了我,痛哭起來。
雖然回到老根據地,困難還是相當大,供給也很差,娘經常翻山越嶺,追趕我們軍區(qū)宣傳隊的駐地,給我們這些“小鬼”帶點煎餅,窩窩頭,老咸菜。一段時期,宣傳隊盼望著“邱大娘”。他(她)們是戰(zhàn)士,也是“小鬼”。
我母親的《登記表》在獎勵與處分欄里填有她一九四九年在嶧縣山陰魯南第五區(qū)醫(yī)院為給病傷員洗血衣受大會表揚,口頭獎勵的記載。
乍一看,我?guī)缀跽×恕R粺o獎品,二無獎狀,這算獎勵嗎?!
隨著這行記錄文字,我的思緒回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滋陽縣工作,父親派人牽來一匹馬,接我到魯南醫(yī)院駐地去看娘,她周身疼痛,在床上打滾。她的病,有相當長的歷史了。
記得抗日后期,我沂蒙山根據地得以鞏固,地方政權相繼建立,地下活動的情報聯(lián)絡工作已不需要,一九四三年,年近半百的母親來到梁邱魯南軍區(qū)后方醫(yī)院,她挑選了為病傷員洗衣服,洗敷料的工作。衣被的污垢,敷料的血跡, 用她那一雙凍得跟蘿卜一樣的手指在水溝中搓洗。她洗到日本鬼子投了降。洗到蔣介石飛到臺灣。她待傷病員如親生子女,她周身疼痛,卻心甘情愿。
母親病好了,她銘記這“大會表揚,口頭獎勵。”
日本投降后,蔣介石發(fā)動了全面內戰(zhàn)。
有一天,母親臉上明顯留有慍色,我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
“入黨了嗎?”娘問我了。
“入黨五年了。”
“你五年了,我還不是呢!跟著黨跑了十六個年頭,我的名都是黨給取的。白色恐怖時,地下黨那么秘密都不避回 我,如今有半個天下,公開了,開會不叫我參加,說我不是黨員,這不……。”
我也不相信,用眼光問父親。
父親早就在笑:“你問伯蘭,誰入黨不得自己要求自己申請,得有黨員介紹,得向黨宣暫,你一樣都沒辦過,非說我是共產黨你也是共產黨,我要是國民黨你也當國民黨?”
“你不夠國民黨那塊料!”
她自己緩和了氣氛:“共產黨好也好在這里,一點面子都不講。這十六年,什么大干部我沒見過,一家人都早入黨了,剩我自己也非按規(guī)定辦事,按規(guī)定辦就按規(guī)定辦!”
不久,母親寫了入黨申請,在李韶九、孫怡然兩同志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五星紅旗升起來了,母親萬分高興,多年夙愿終于實現(xiàn)。她同父親都調到滕縣專署醫(yī)院,仍然挑選了洗衣這份工作,在登記表的職務欄,她讓人填上 “工人”兩個字。
建國后,干部的待遇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母親高興極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她還能拿薪金。評級會上,她問:“最高是哪個級?”
“最低呢?”
“那我要二十六。快六十歲了,要那些錢干什么?我要二十六級。”
醫(yī)院的污物桶里,每天都有很多繃帶、敷料,母親看見心疼,她都撿出來,洗凈血污再煮沸消毒,下次再用。結果,她感染了。完全喪失活動能力,癱瘓了兩年,農民出身的母親體質好,經治療后能下床了,但已不能勝任“洗衣工”這個職務了。
一九五八年,六十五歲的母親同六十八歲的父親同時在北京退休。
父母喜歡中華民族的象征——泰山。經自己要求,有關方面聯(lián)系,他們遷到泰安定居。
一九六九年,我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離京去湖北途中繞道泰安,母親對我說:
“前些時,北京來了兩個臂帶紅袖章,穿黃制服的人,由管理員領著來找我。我一聽北京來的,準是你郭叔惦記著我,派人來看看,連忙招呼打聽起來,可這兩個人說是姓“吳”(無)的司令部派來的,是調查郭子化叛變投敵的歷史材料,還要我同你郭叔劃清界線。我一聽就火了,也顧不得講客氣,我說:“叛徒!你倆見過嗎?當時還沒出生吧。”我七十五了,怕他怎的,我說我見過叛徒,一個三八年叫我們抓住了,老頭要用槍打,是我叫用刀砍的。另一個佟振江解放后抓住,也是我老頭寫材料定的死罪。這兩個叛徒害死了田位東、鄭乃序。郭子化叛變害了誰?!這兩個人說是調查一九三六年端午節(jié)的頭幾天,郭子化被一個姓米的叛徒逮走的事。我說:
“這事我知道,是李韶九和我老頭幾個人商量保出來的,出來后就跑到山里,以后拉起隊伍打游擊,是叛徒還要我們保!!還要跑!!”這兩個人還沒個完。
我見他們胸前的像章就問:“你倆戴誰的像章?”他說:“是毛主席的。”我說:“不對,不是毛主席,休養(yǎng)所給我送來的毛主席都有領章、帽徽。”他說:“這是什么時侯,是軍閥統(tǒng)治時期,去安源還沒上井崗山呢,哪來的領章帽徽?”這可叫我有話說了:“你剛才不講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條件?毛主席這時為什么不打出共產黨的旗號呢?后生,黨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去問問你的祖輩吧。”
兩個人沒話說了,也沒叫我按手印,走了。我連夜趕到兗州,找你哥哥伯達——他還在靠邊站,時刻準備挨斗,我叫他只說一句話:“什么也不知道。”
我在干校“畢業(yè)”回家前,提前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問她需要什么?
回信開的單子是小電燈泡兩個,長釘十枚,火柴一包。
回到泰安,我拆開一包“孝感麻糖”遞一片到她嘴里,娘說好吃。當她知道是一元多一盒時又不高興了。說我亂花錢。
母親晚年有舊的習俗思想,安排死后與父親合葬,要我嫂子為她準備了一口棺材,我們動員她發(fā)揚老一?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質,帶頭移風易俗,不用棺材,實行火葬。因剛實行火葬,還有阻力。母親開始有些猶豫,后來還是同意了。說黨員就要聽黨的安排,立即把棺材處理掉。
泰安地委高書記常去探望邱大娘,知道了我母親是二十六級的“干部休養(yǎng)員”,在三中全會后,他和地委組織部商量,同北京中醫(yī)研究院——母親原工作單位取得聯(lián)系。一九八〇年八月,地委組織部以中央有關規(guī)定和負責同志講話精神,決定將我母親由行政二十六級改為十七級。
這時,八十六歲的母親已經住進泰安人民醫(yī)院。
我從北京趕去泰安時,母親已病危。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母親就逝世了。
對后事的安排,母來臨終告誡不舉行任何悼念儀式,謝絕任何親友送花圈,要將骨灰同父親合葬在一起。
泰安縣老干部辦公室發(fā)出吳洪起同志逝世的《訃告》中提到:“吳洪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zhàn)斗的一生。”
(孫贊勛整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北京
編者注:
邱伯蘭,女,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生。山東省棗莊市齊村人。一九四〇年八月參加魯南軍區(qū)宣傳隊,一九四二年九月入黨。歷任宣傳員、教師、費縣縣委文書、魯南四地委股長、平邑縣團工委、副書記;歷任嶧縣團工委副書記、陶莊煤礦團總支書記、黨委組織部副部長、棗莊礦務局組織部副部長,阜新煤礦學院組織部部長。一九六五年調北京,一九七二年調故宮工作,現(xiàn)已離休,住北京。
原文刊登于《棗莊地區(qū)黨史資料(第四輯)》,中共棗莊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1986年8月)